当代社会的文化矛盾
—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丹尼尔·贝尔是当代美国重要的学者与思想家,他在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化学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他对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揭示,以及对于造成这种矛盾之原因的分析,对于今天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有着较大的借鉴意义。虽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以后,产生了一些与资本主义相似的社会现象。因此,研究和学习贝尔的这本著作,其意义就决不限于隔岸观火式地了解一种制度,或者作为论证资本主义腐朽性的又一证据。而有着较为普遍的现实意义。此外,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所运用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的学者拓宽研究思路、探索研究方法,也有可资借鉴之处,特别是在今日各学科壁垒森严的情况下,贝尔却在几门学科中纵横驰骋,充分发挥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优势,值得我们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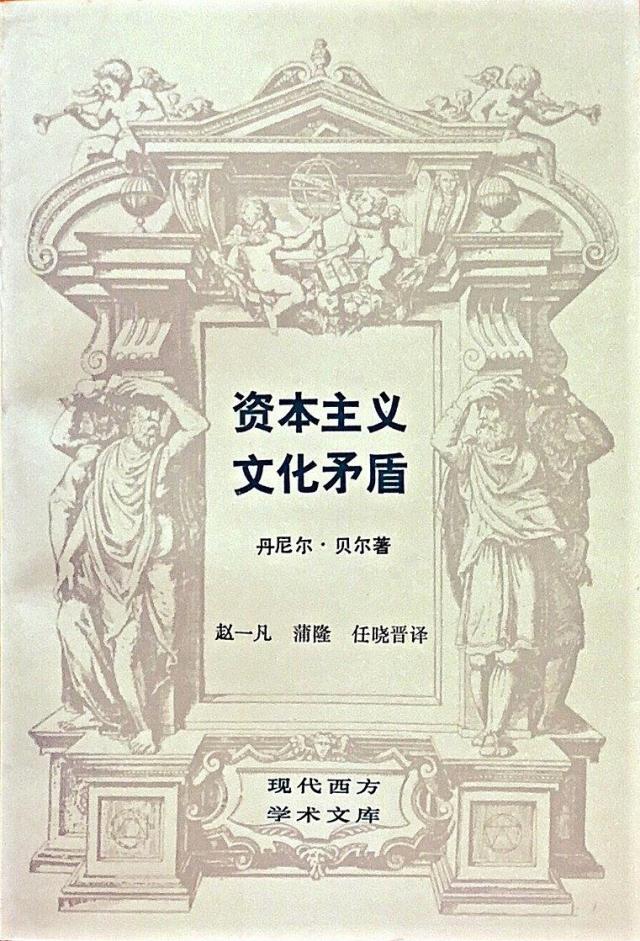
贝尔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所在,是其内部结构的脱节与断裂,这一矛盾最突出地表现在资本主义内部“三个领域”的对立上。首先是经济领域内部的对立。经济领域这个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基础部门,其全部活动都严格按照“效益原则”运行,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在这个日趋非人化的体系中,人的丰满个性被压榨成单薄无情的分工角色。作为补偿,这个日益强大的技术与经济共同体又宽宏无度地许愿社会进步的奇迹,提供广泛选择就业和社会流动的自由,促进社会享乐倾向。其次是政治领域内部的对立。表现为广为派生的平等观念和各种民众要求与过分庞大的政府机构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为了适应这种不断深化的平等要求(如种族与性别平等、教育、福利平等),政府被迫扩大官僚机构,另一方面这些要求逐步将传统政治代议制扩展为基础宽大的直接参与制。这样,公众与官僚机构间的矛盾就成为大问题。第三,也是最为严重的对立来自于经济基础和那个“更高地悬浮在空中的思想领域”(也即文化领域)之间的对立。与经济和政治领域不同,在当代资本社会,文化领域起支配作用的既非“经济效益”,也非“平等权力”。艺术和思想的灵魂是所谓“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文艺家常常标榜“个性化、独特性”以及“反制度的”精神。西方现代派艺术更是对资本主义传统价值进行无情的批判和嘲讽,建立起与经济体制严重冲突的“文化霸权”。
造成这些矛盾的原因,贝尔认为是由于资本主义精神中“宗教冲动力”的丧失和“经济冲动力”的膨胀。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这两股力量互相制衡,苦行的宗教冲动力造成了资产者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风范,贪婪攫取的经济冲动力则养成了他们挺进新边疆、征服自然界的冒险精神和勃勃雄风。但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代表着宗教冲动的禁欲与节制精神逐渐被法制、现实主义文学、实用主义哲学和科技理性取消了存在的合理性,接着又被二十世纪的新文化运动、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等享乐主义观念消解了道德伦理基础。而当资本主义制度只剩下“经济冲动力”时,文化矛盾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由于限于本文的篇幅和个人的学力,我在本文中仅结合我们当下所处的实际环境,对贝尔书中所论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第三个方面谈一些个人的感受。
与西方中世纪以来的传统不同,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教的影响力不如西方强大。既没有与世俗权力对抗的教会力量,也缺乏西方社会那种一神崇拜的宗教。在中国,有儒释道三教,三教互补,构成了中国人的基本信仰。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儒家。(儒家思想能否算宗教,还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而且,既便是一种宗教,一般也认为,儒家思想是一种道德宗教),弘扬儒家思想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阶层——土大夫。土大夫既是国家的管理者,又是文化的传播者,他们认为自己在传播文化方面负有使命。正是他们的努力推广,使得以儒家思想为主的精英文化成为很多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文艺对中国人的思想与心灵的陶冶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中国传统文艺观点不强调文艺的独立性,以推崇“纯文艺”,而强调“文以载道”,认为好的文艺作品必须传达君子的思想或价值观。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文艺大国,仅就诗歌这种体裁而言,其数量就非任何一个国家所能比,(举一个例子,陆游一人就有诗九千多首)。这样,文艺的繁荣,势必形成精英价值观向民间的扩散。所以,中国文艺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构建影响巨大,林治堂甚至认为诗歌(文艺)代表替了宗教的任务。我们在古人诗文中常能读到了“游子思妇”、“英雄迟暮”、“美人漂零”、“沙场征战”、“怀才不遇”、“死生契阔”等主题都是对痛苦现实人生的一种关怀。因此,中国人除了广义宗教关怀外,还有一套人文关怀系统,来安顿人类的心灵。但是这种传统的系统在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先是在“五四”时期遭遇了一次“硬伤”,主要是“新文化”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合理化产生了怀疑。进入新中国后,文艺的现实关怀作用又受到了一次打击。文艺常常作为一种政治宣传工具来使用,因而进一步“意识形态化”。20世纪50年代有一篇小说,在当时曾引起很大反响,那是肖也牧先生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具有小资情调的男人和一个革命干部出身的女人结为夫妻后,在价值观、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方面,由矛盾到适应的过程。小说对小资产阶级生活情调基本持批评态度,但由于任何适应都只能是一个互相适应过程,小说必然也会对这种互相适应有所反映,所以此文后来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受到了批判。这个故事如果让今天推崇“小资情调”的青年去读,不知会读出什么滋味来。文艺在上世纪80年代曾有过短暂的辉煌,但毕竟不可能象传统文艺一样,足以影响到人们的精神状态,甚至起到“安身立命”之作用。所以文艺传统的作用越来越弱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业文化作为强势文化,粉墨登场,一些文化人甘心沦为附庸,为商业文化的摇旗呐喊。铺天盖地的广告,形形色色的快餐文化、各种即兴娱乐节目、肥皂剧、无厘头电影、构成了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白领文化,这些文化并无多少思想内容,而只是劳累一天后简单的大脑放松游戏。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变得越来越困惑,找不到方向。商人们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所谓精致、高雅生活的幻影,而这种幻影又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某种难以言说的期待(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作比较,西方社会当然也有强势的商业文化,但我们却没有被贝尔称作“文化霸权”的现代文艺,这种文艺虽然表现出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却无疑具有对现有制度的批判精神)。但如果说,我国的文艺家都是商业文化的同谋,那也言过其实。一些有思想的文艺家也在不断地努力,但在强大的思潮和时尚面前,他们却只能不断妥协,由于妥协的部分过于突出,思想内容有时反而隐而不显。这里可以举张艺谋的电影做例子。张艺谋从最早的《红高梁》开始,其影片在国际上屡得大奖,可谓得奖专业户。事实上,张也确实是一个有追求的电影人。但在国内,真正理解他影片的人并不多。以早期的《红高梁》为例,相当多的人认为这是一部宣传愚昧,不惜出丑以邀宠的片子。中期的《我的父亲母亲》,反响平平(我个人认为该片是张艺谋拍得最好的影片),一个村里最漂亮的少女爱上了一个乡村小学老师并结了婚,女孩子没有什么文化,每当他先生讲课的时候,她就站在教室外听,这样一听就是几十年。很多人认为这是一部拍得非常精致的带有童话色彩的爱情片,而完全不顾及老谋子重建“文化至上”的良苦用心。耗资巨大的《英雄》,对其评价虽然众说纷纭,但总体来说并不讨好大部分城市电影观众。此片既不象武侠片的路数,又非言情片的类型,虽然场面异常宏大,镜头异常精致,但观众似乎不知道老谋子想说什么。这里,张艺谋想要表达的个人情感,利益及其超越的问题(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也就是张艺谋想成为哲学家的那些内涵,并不能引起共鸣。张艺谋最大的特点,是其驾驭场面以及让影片多主题变奏(用过去的话叫雅俗共赏)的能力。一但多主题变成了单调,变成一种哲学思考,而浅显的娱乐不足时,观众马上不干了。这也说明,既使包装得再好,今天的高雅文化也已不复往日的雄风了。其他一些有社会责任感。有追求的导演所拍的电影往往更不卖座或沦为小众电影。
行文至此,便产生了另一个问题,本文多谈文艺,但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传达思想的并不仅仅限于文艺。更重要的哲学哪里去了?或者说思想家那里去了?这里就不得不接触到另一个问题,也就是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提到的研究方法问题。由于社会的分工日细,学术研究正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微观。过去博古通今,在各领域纵横驰骋的思想巨人、通才大儒已很难产生。往日雄鹰般的宏观研究已为土拔鼠式的狭隘经营所取代(见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译序)。各专业之间彼此壁垒森严,形同河汉,老死不相往来。一些德高望重的专家在自己的领域内可以呼风唤雨、游刃有余,具有绝对的话语权,而一出此领域,马上变得“失语”或“乱语”。在对待大众文化上,更是缺少关注的热情和引导的使命感。曾有人调查北京几所著名大学的教授对大众传播媒介电影的兴趣,结论是很多教授几乎从不看电影。这种对大众文化的漠视,使得他们在大众文化领域根本无法置喙。反过来,有些专家则以专业化的标准来要求文艺和要求大众文化。近几年来引起广泛关注的“余秋雨现象”就是一个例子。这个以《文化苦旅》、《一个王朝的背影》等散文集引起轰动的作家,也许本来无心做一个历史学家或哲学家,但很多专业人士都以专业的眼光和专业的标准,纷纷指出余文中的许多思想失误和细节疏漏,对此,余作了很多回应,不幸的是,余并非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去回应,而是以一个历史专家的身份来回应。久而久之,余秋雨可能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哲学家乃至历史学家了。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姑且称之为“黄仁宇现象”,这个以《万历十五年》在大陆出名的美籍历史学家,因其所使用的都是“描述语言”而非“分析语言”,他研究历史的方法又是所谓“大历史观”,所以常常被国内一些历史学家视为空疏,一直到其《明代财政研究》出版,证明其具备较为严密的考证与分析能力。空疏的指责才稍有减弱。事实上,学术作品的使命不是单一的,学术也有面向大众传播思想文化的义务,因而其表述方式也可以是多样性的。不过,我们也必须对用媚俗的方法来提高知名度的某些文化现象保持应有的警惕。以上这些想法,可看做我们阅读丹尼尔·贝尔著作所引发的思考。
参考文献: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
撰稿 黄意明.编辑 曾石如,图片来源 网络